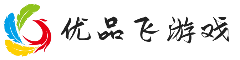大平台全新升级 大品正规官网 房卡 欢迎咨询 专注十年老店!!!
玩法详解:
2、打开添加微信客服【353508984】
注意事项:
文 | Pavo
编辑 | 珍妮
1
从这一刻开始,外婆一睡不醒。
我们都知道,她很快就将开展一段新的旅程。
一个朋友曾经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人一旦大限将至,会先梦到一些属于“那个世界”的东西,之后便不会再害怕死亡。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是缘于未知。如果捅破了这层未知,便没有什么好再怕的。
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从外婆口中得知她实际的感受了。是否她已经先一步去那个世界探险过?是否也有先人和她在梦里交谈过?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灵魂仿佛嵌在生命之门的交界处。她的表情往往如梦似幻,我想她并不活在当下,而是已经部分地超脱了俗世沉重的躯壳。
2
外婆是突发了大面积脑梗,昏迷不醒而被送到了医院。
她年事已高,在此之前久卧病榻。因此对于她也许救不回来这件事,我们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她本人没什么痛苦。”急诊室医生点点头,似乎觉得这个动作可以为我们带来一定的安慰,“你们照顾得很好,老人身上我一看就知道的,你们是一直在照顾的。”
我妈妈和小舅舅立马红了眼眶,看护老人是一个持久、看不到尽头且没有任何回报的项目,等待着人们的只有终将到来的绝望。这位医生,也许他是真心认为应当鼓励这种人类的反哺行为。
“不大会醒来了,你们应该都有心理准备吧。”医生又说。
他建议我们不需要费心再去沟通病房了,并允许我们将外婆目前所躺着的一张病床放置在急诊室门外的一侧。那边是一个敞开的空间,而医院里人来人往,一张床榻多少是有些阻碍到空间动线的。
所以这个建议也相当于告诉我们:时间不会很长,也许都过不了这个夜晚。
3
我看着病床上的外婆。她安静地躺卧着,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甚至因为久未出门,皮肤都变得细腻光洁,看起来苍白而透明。从人们临终的脸庞,你往往难以推演出她年轻时的容颜。如果要我描述回忆中外婆的脸,那是一张福气满满、国泰民安的脸,好像生来就刻上了“慈祥”两个字,是饱满而鲜活的脸。
现在躺在病床上的这个妇人,就好像是偶然地戴上了这样一张面具,半透明的、了无生机的面具,悬浮地挂在她的脸上。
我印象中最年轻的外婆,应该也已接近花甲之年。曾经她是一个卷曲短发、身形稍胖的妇女。我会在每个星期天跟随父母去探望她,在漫长而无聊的下午,跟着她看译制电影。我记得她喜欢看动作片,会在正派角色打出致命一击时大声叫“好”。而在这样的剧情高潮部分,我的爸爸妈妈通常正在忙着帮她做家事,烧饭做菜、料理家务。
忘记过了多久,医生宣布说外婆离开了。
4
我妈妈先开始哭了,这让我心里一紧,本能地开始想着要如何应对。她抓住我舅妈的手流眼泪:“我没有妈妈了。”她需要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这我一直都很清楚,在照顾外婆和陪伴童年的我之间,她几乎永远是选择外婆的。我走过去和舅妈一起安慰她,外婆也可以说是“寿终正寝”,按照医生的意思老太太有福气,她最后的时刻都没有吃什么苦头。
外婆就这样,在她的梦境中与我们不告而别,她沉默的神识在梦里曾经遇见过什么,即将有什么样精彩的经历,我们往后再不能知了。
但对于妈妈来说,痛苦才刚刚开始。退休后的她每周会匀出大约四个白天,与舅妈和护工一起来照护外婆,以后却再不能够了。她业已建立的日常规律正在坍塌。
更让她无所适从的是,如今她没有了妈妈,她再不能成为一个女儿。不管是任性的女儿还是乖顺的女儿,只要妈妈还健在,一切总还是有可能的。
接受外婆的离开,像缓慢地撕开一层贴了很久的创可贴,皮下有隐隐的疼痛慢慢才会泛上来。我现在回想起来,在外婆真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她在世间的气息已经相当模糊了。
5
淡忘,不像是一场葬礼,会有一段音乐和一次演讲来宣告天下。它往往是在其完成式时,才被人认识到,从而在心中再添上一种名为“遗憾”的情绪。
当外婆逐渐开始剥除她作为社会人的种种属性,我们这些儿女、孙辈便开始淡忘她。
可最开始无人意识到这一点。
6
每一年的除夕、国庆假期、五一假期我们是例必聚餐的,大家会空出完整的一天用来相聚。家族的习惯是每个子女各负责几个菜,愿意一展厨艺的便在厨房干得热火朝天,想要偷点小懒的就外购几盒熟食比如酱鸭、酱牛肉一类。外婆有一张宽大的藤椅,聚会时的白天,她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坐在上面,我们则在一旁陪她看电视和唠嗑。
然而在最后的这几年里,大家开始变得懒于在家里开灶用餐,转而投向家附近的饭店。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
最开始,外婆也会和我们一起去到饭店用餐。但有一次她吃完饭要回去时,她的大女儿,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姐,把一些没拆封的湿巾塞到她口袋里,让她带回家。她一下子就发起火来,举起她的拐杖,极其用力地敲击地砖,表示自己根本不想要这些。我从未见过如此震怒的外婆。她愤怒于自己现在的状态,不想要这样受人摆布,于是把所有的怒气聚焦到了这一刻来爆发。湿巾只是导火索。
7
那次之后,外婆就不去饭店参加我们的聚餐了。逢到节假日,我们会在去饭店聚餐之前,分不同批次和藤椅上的外婆会面,之后会留下两个人来陪伴留在家中的外婆。
餐桌上的话题,在开头会说一下外婆越来越糊涂,但话题在大约五分钟后便会发散开来,覆盖家长里短和时事政治,比如埋汰一下自家孩子这次没考好、吹捧一下别人家孩子真是个人才、在某个心照不宣的范围内骂一骂领导人,诸如此类。
8
外婆的沟通被切断了,她变成了一个信息交流的终点站。
淡忘,就这样发生了。
看顾她的人后来才意识到,越是用心照护她的起居,在意她生理上的各种指标变化,却离他们曾经拥有的妈妈越是遥远。外婆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因为缺乏基于当下的交流,外婆毫无还手之力地被解构为了“需要悉心养护照顾的躯体”。
我们这些人,是她这个“生命之源”流淌出的结晶,可是我们也都出于生命的本能背向她行走,渐渐走出自己的路,将她抛诸脑后。
9
当然,不仅仅是我们在行走,其实外婆也仍然奔走不息。就仿佛是知道即将踏上一段新的旅途,临终前的几年,所有属于当下的一切,概不会在外婆的海马体上留下烙印。
她的认知先从她衰老的壳里挣脱出来,不管不顾地奔涌在回溯的路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过的,是她曾经的青葱岁月。
她开始频繁说起过去。在她的叙述中,她是逃了学堂的课去河边吹短笛的小孩,光了脚丫踩在泥里,完全没想过回去会怎样被骂;她是在女伴怂恿下偷偷跑了好远路去看结亲对象的少女,撂下一句:“倒不是麻皮跷脚。”就转身跑掉。
在精神层面,她是生命的逆行者。她是老了,可是她的世界又慢慢地年轻了。
在那个于我们而言十分陌生的世界里,外婆是一个任性的小姑娘,她不是一大家子的“祖宗”,不是谁的妻子,也不是谁的妈妈。
10
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看的电视剧《封神榜》。商王朝的皇叔比干有“七窍玲珑心”,狐妖妲己为了除掉这个和她不对付的忠臣,用计挖出了这颗心。
挖心之后,电视剧接下去的镜头跟随着比干,一路走出大殿,走出王宫,走到街上。他看起来与一个耳聪目明的平常人无异,直到遇到一个卖空心菜的女人。接下来的对话我们都很熟悉了:人若无心呢?
仿佛是突然意识到他已是无心之人,比干这才倒下死去。虽然在大殿上,按理来说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生理性死亡。
人死了,他的感官仍然活跃着。这件事是反常理的,因此被拿出来浓墨重彩,以一种荒谬的写意凸显情感上的震撼,从而令观众更能够惋惜比干之死。
而更为常见的是另外两种:其一,人死于意外,其感官瞬间全部关闭,意识也同步关闭;其二,因病或自然衰竭而死,感官会陆续关闭,最后是意识。
11
关于后者,我想用一个形象的比喻:
日落西山之后,死亡带着风进入人的城堡,先是无序地吹上各个房间的门——那些房间里居住着各种感官,它们从此沉睡。最后这阵风钻入了走廊深处的最后一间房,那里居住着人的意识,风“噗”地一声吹灭了房间里点燃的蜡烛,意识从而也遁入了无边而永恒的黑暗。
外婆没有遇上意外,也没有罹患重病,但她的身体抵抗不了自然规律,正在逐渐地衰竭。死亡的这阵风在进入外婆的城堡时变得格外温柔,也许是它并不赶时间。
于是属于感官的那些房间,门总是半开半闭,隐约而模糊地与外界有一些链接,有时甚至门还更敞开一些,给人不必要的误解,觉得自己竟能逆转自然的规律了。
但最终,它们的门都会关上,那一刻终将到来。
12
最先背叛她的是视觉。
青光眼送了她十层薄纱,即便手术后,她也看不了密密麻麻的字了,而原本她每日主要的休闲活动就是看书。她喜读小说且看得杂,看《三言两拍》,也看琼瑶,甚至看席娟。无法看书之后,那些八卦狗血小故事、你侬我侬的爱情,都离她而去了,她听见一千个小星球在“噗”地熄灭。
有一两年,也还能看会儿电视,但眼疾终于将世界的鲜艳与锐利隔绝在外。不知从何时开始,画面变成了一些色块的移动,是否需要将视线固定在某个特定角度投于屏幕上,已经不重要了。
13
随后听觉的房门也开始响起可疑的“嘎吱”声,是风来了。
她觉得就好像有股力量领着她走进一个山洞,外界的声音渐渐都变成模糊而意义不明的呓语。坐在她身边与她对话时,人人都提高了音量,方能维持住正常的交流。有时需要凑近她耳边,尽量大声去叫她,就像站在山洞口,喊一个玩得心野了的孩子,喊她回家吃饭去。但她没法出来,山洞磁石一般地吸住了她。
当感官的房门逐渐关闭,她的卧室也开始变得安静。因为电视也变得不再具有吸引力了,电视开着发出无意义的声响,这会令她感到异常烦躁。她生气的时候就躺下来,把脸朝向墙壁,眼睛紧紧闭着,像一个赌气的小孩子。
我想做子女的永远无法真正安慰到一名老人,正值盛年的他们如何能感同身受呢,他们的城堡正宁静无风。我们看着她的一头银发,都不敢响。
14
风一旦吹起来,就不会停止。
外婆的内脏器官逐渐开始出现一些称不上大病的小问题,如果去看医生,他们会告诉你这是衰老导致的,就像机器用多了总会磨损,无可避免。她有胆囊和胃的问题,这两件器官的功能减弱了,导致她无法消化许多人类公认为美味的食物,比如红烧肉、海鲜、高热量的甜点。如果她仍然维持原先的三餐习惯,那么到了夜里她会腹痛到难以自抑,甚至需要到医院挂急诊。因此,晚上的这一顿什么时候吃、吃什么、吃多少,是作为主要照护者的我妈妈和舅舅、舅妈重点要关注的问题。
但人总是这样,越是被拒绝,越是想要拥有。每天的晚餐时分,外婆经常为了多吃一块肉而斗智斗勇。我妈妈进行严格的管理,说一不二的风格让外婆感到气愤,有时甚至会生气起来。
对此,妈妈认为是外婆一生都被“娇养”导致的。“她当了一辈子的娇小姐。”
15
外婆有七个孩子,曾经有过八个,其中一个在五岁时候夭折了。提起那个孩子,外婆不无遗憾。那是个女孩,十分漂亮乖巧,但身子弱,有哮喘。有次女孩咳嗽,外婆让她自己吃一片橘子。片刻后外婆发现房里极安静,转头一看那孩子竟已死在了椅子上。
“可能是一口痰卡住了。”外婆后来跟我聊起的时候,自己推测说。
实际的原因无人知晓,那孩子夭折的时候太年轻了,后来也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墓,家里人用草席包了就处理了。痛苦只停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那个年代痛苦要去的地方太多了,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它逗留许久。
16
我妈妈为这个故事添加了一些注释,她说外婆实际上是不会养孩子的。外婆是绍兴乡下人家的二小姐,一直到她的青年时期都没做过什么家事。头两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家里还富,奶妈和长工没有断过,长辈又极宠,真正是一点苦头都没吃,在照顾人上出点小纰漏再正常不过。
而为了增强这个注释的合理性,她又告诉了我另一个故事。
妈妈手肘上有一块陈年的伤疤,小时候我喜欢摸着它入睡。妈妈告诉我关于这个伤疤的有趣故事:外婆家过去曾经住在海防路,是沿街的那种二层楼房子。一次妈妈上屋顶玩的时候摔伤了手肘,回来告诉了外婆。外婆推推眼镜说“没关系,我来处理”,然后帮妈妈涂了药水。涂完痛得要命,仔细一看才发现涂错了药水——是随手就拿了一瓶脚藓药水抹了。
我们现在对“妈妈”这个身份有一些含有褒义的印象,比如“神不能无处不在,因此它创造了妈妈”。但实际上,人并不是一当上妈妈,就自然而然地跳入这个充满神性的躯壳中的。
17
是的,在我不幸未能长大的姨妈和我妈妈出生的年代里,外婆家里开始请不起佣人了。家里孩子太多,外婆和外公又都有工作,根本照顾不过来。
所以妈妈最初是被过继到亲戚家里的。后来我的舅舅,她的二哥去乡下探望,发现她被养得病怏怏的,又瘦又黄像一根麻杆。二哥一看就急了,回家闹着要把小妹妹接回来。
儿子的话到底还是有一些影响力,妈妈就这样回了家。
我也一直很好奇,妈妈生命最初的底色是谁铺就的?但妈妈从未提起过最早养她的那家人,我想也许她也早已忘记了。她的人生就从回到外婆身边开始。
18
由于不断地生孩子,再加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运动和自然灾害纷至沓来,外婆的身体一点点垮下去,她老年时期的慢性病和器官衰竭也就此埋下祸根。
但外婆自有她的幸运,瞧,至少孩子们是懂事的。
外婆的孩子多,年龄跨度很大。我的大姨妈比妈妈要大上十来岁,她少女时期就开始承担家里大部份的家务事。再过个几年,姨妈结婚了离家住了,那么我妈妈又长成了,可以接棒过来,继续照顾这个家。
外婆全身心投入工作,教了一辈子的书,加班回来,孩子给她煮好饭,照顾好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再陪着她在灯下再批一会儿作业。每年会有一次,当她在“阅”后面写上日期时,她会意识到这是她小儿子的生日,那天是11月11日,特别的数字组合。因为孩子太多,她根本无法记清每个孩子的生日,更不用谈生日的仪式感。另一个有幸能被她一年一度在生日当天记起的幸运儿,是我妈妈,她的生日在10月2日,恰好是国庆节之后一天。
19
我从懂事起就发现,外婆家和我父母的家是密不可分的。我妈妈具有卓绝的责任感,她像是一个长大了却还不愿意剪短脐带的婴孩,幻想着能够把营养通过这个管道再输送回去。小时候我闹着要妈妈陪的时候,有很多次她都会告诉我,没有办法,她现在要去陪着外婆,外婆身体不好。
还有一件事,也是她为此骄傲并反复提及的,当时外婆怜她瘦弱,订了每个月的牛奶给她喝,但她去偷偷退订,把钱拿来补贴家用。
结婚生子后,妈妈仍然维持着每周探望外婆的习惯。她带上爸爸和我,在过去那个没有轨道交通的年代,每周单程花上两个小时挤公交车前往。然后在外婆家之后马不停蹄地开始干活,煮饭烧菜,整理家务。
20
我当时非常期待每周可以去外婆家。
虽然往返四个小时的路途在现在看来漫长得近乎恐怖,年幼的我学会了分别用雀跃的心和回味的心来填满往返程,使路途变得不那么枯燥。
外婆家是一楼的一间小小公寓,在童年的印象里是永远明亮,充满了惊喜。上午的时候可以溜出去在社区花园玩,用叶子铺成坐垫,在假山里玩捉迷藏。下午开始有些无聊,就跟着外婆看电视里放的外国译制片,那些外国男人对我来说长得都差不多,我唯一能认出的是小小的秀兰邓波儿。
而在我玩玩闹闹,和外婆看电影的休闲时光里,我妈妈在烧饭做菜、料理家务。这是我和外婆亲子时光永恒的背景音,因为习以为常,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都意识不到。
在时光的水里擦掉颜料,我看到你了。
21
有一些记忆片段,总是冷不丁地在我脑海中主动浮现。
我认为它们也许是商量好了要悄悄绕开我妈妈,也就是长大以后,我学会了把它们在时光的水里洗上许久,然后仔细端详。
在我的印象中,外婆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被照顾者。可是也有一些场景中,她她作为一个独立的、能够掌控局面的角色出现了。
那天我听见敲门声,开门发现一个卷曲短发、身形稍胖,身着蓝底白色印花上衣的女性站在门口,手里提着半只鸡,以及一些蔬菜。这位便是我的外婆,她没有事先打电话告知,就这样风尘仆仆地跨越了半个上海来了我家。
她放下手里的菜,脱鞋坐下来准备喝一杯热茶。
妈妈看到她,脸上显出讶异的神情,问她怎么就这样跑来了,之前没说过呀。外婆含含糊糊地顾左右而言他,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她没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多年后,年迈的外婆因脑梗入院。看到她沉静地躺在病榻上,不知为何她穿着蓝底白色印花上衣,提着半只鸡的形象又闯入我的脑海。这次它仿佛在叫着:“记住我。”
那么这个愿望成功了,我心想。这世间凡是未解之谜,总是更容易被人记住。
外婆当时已经进入沉睡,没有机会再去问她当天为什么去到我家。也许和外公吵架,也许和同住的儿子吵架,又也许只是想看看自己的小女儿。
22
在另一个片段里,我们搬了新家的第一年,邀请外婆来小住。
我还记得她坐在庭院小板凳上的背影,彼时已是头发花白。现在让我们绕到她的正面去,看看她在干什么呢?你也许会像我一样吓一跳,至今那个画面在我的记忆里仍然是被屏蔽掉的。
画面被抽掉了,换成一些文字叙述来记录吧:外婆是在杀鸡。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是的,多奇怪啊,平时她都很少烧饭做菜的,可是她掌握了“杀鸡”这门在我看来是料理中的终极技艺。
外婆杀的那只鸡,并不是当天菜场采购的活禽。那段时间我妈妈不知为什么迷恋上了养小鸡,有一天她下班回家,从路边买回来四只金黄色毛绒绒的小鸡仔。这种鸡挺难养,容易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出于各种不明原因死掉。果不其然,才到第三天,其中两只鸡病怏怏地看着命不久矣。可没想到当天晚上,妈妈又补充购买了两只新的小鸡。
就这样,总有小鸡死掉,也总有新的小鸡被补充进来。一段时间后,有一只健康的鸡活得比较久了,它渐渐褪去了幼态的那种金黄色的绒毛,开始长出较为粗硬的褐色羽毛。身形大了,腿也长了,是一只少年鸡了,从它身上你能隐约辨识成年母鸡的样貌。
23
就是在这个时候,外婆来了。她应邀来小住几天,但在接受邀请前她倒没有想到家里会有一只活鸡。
外婆告诉我妈妈,这鸡差不多了挺大了,可以杀了吃了。妈妈倒不是对鸡产生了感情,只是她虽然有着丰富的料理经验,但还不曾亲手斩杀过一只鸡。于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像一个小女孩般对着外婆撒娇,说我不敢呀,这怎么弄啦。
外婆说了一句我认为是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我来杀。”
好的,您请。我妈妈立马递刀,然后退出现场。
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坐在小板凳上背影的前情提要。
外婆是真的会杀鸡的,她处理得挺不错,后来那鸡被烧成了一盘咖喱鸡块。只是很难回忆起是什么味道,我和妈妈都没太敢吃。
像这样一个果敢利落的外婆形象,在我的记忆里也是很罕见的。但当我梳理回忆,把这个形象和那个看动作片大声叫“好”的女人重合在一起时,又忽然变得合理起来。
24
在外婆住在我家的那些时光里,我总是快乐又拘谨。
快乐,是因为外婆。
只要外婆在家,我妈妈就会下厨烧很多好吃的菜。平时我的晚餐通常由我爸来煮,有营养但无创意,不是一个小孩会喜欢的样式。
妈妈因为平日里下厨的机会并不算多,因此很好地保存了对料理的热爱与激情。当时电视上美食料理节目已经开始流行,她会认真观看,然后记下其中的诀窍,在我们的餐桌上进行复刻。经由她烹饪的饭菜有两大特点:重油且甜口,算是本地菜肴浓墨重彩的呈现。很早之前她就会在炸鸡翅里拆掉一根骨头,塞入剁碎的虾仁、糯米、酒酿等等。
妈妈下厨的时候,我喜欢往来于厨房和客厅。一边是炒着菜的妈妈,一边是戴着老花眼镜看书的外婆。我执着于研究今天有些什么菜,几道荤的几道素的,现在烧好了几道,并把这些消息陆续汇报给外婆。我应该是打扰了外婆看书的,但她并不恼我,还是笑着,句句有回应。
厨房里爆炒的嘶啦声因为门开门闭而时而渐弱,时而渐强。
25
拘谨,也是因为外婆。
对于我,外婆有极其厚重的滤镜,在她的表述中,我是一个极好的小女孩,我是漂亮的、爱学习的、无比自觉的和思想成熟的小女孩。
我爸要求我在假期进行自我规划,每年假期开始我们都会制订一张每日计划表。我把这张表当成一份重要的项目,规划精确到分钟,列名了所有要做的功课,要学习的技能。
某天外婆的闺蜜来看她,她们就对着这张规划表议论起我来,说这孩子有多自觉啊,是一万个里面都找不出一个的好孩子。我坐在房间里,隔着门静静地听着她们的讨论,功课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外婆的褒奖让我感到受之有愧,于是更加不敢露出自己的一点点不好来,每天花很多时间躲在房里,作业下面却偷偷放着言情小说来读。
我受到了无形中的规训,外婆的存在让我时时刻刻要审视自己,有没有达到了她心目中这个完美模型的标准。
26
我先将画面定格在这一刻吧。
在我的家里,有爸爸妈妈和外婆。颜色是明亮的,气味是甜甜酸酸,画面中的人微微有些紧张,想要完成彼此眼中的形象,踌躇着应该摆什么样的姿态。
在快门将按未按之时,时钟的嘀嗒声却愈来愈响。
过去的时光被折叠起来放好了,现在即将要走下去的这条路,其起点是外婆的死亡。
在急诊室门外我握住妈妈有点凉的手,外婆的形象更加清晰我现在可以看见三个“外婆”的形象。第一个作为“妈妈的母亲”存在;第二个作为“我的外婆”存在;第三个则是一个模糊的我触不到的影子,是少女时的外婆,只出现在年迈的她自己的叙述中。
27
在急诊室门外,我握住妈妈有点凉的手。
此时有一个赤着脚的少女笑盈盈地走过来,手里抓着一枚短笛。她很快变作一团模糊的影子。这是我未曾认识的外婆,她只出现在年迈的她自己的叙述中。
她先走远了,没有留恋的样子。随后我看到妈妈也直起了身子,看向前方,我猜她看见了她的妈妈,也许是中年妇人的样貌。
想是那妇人也远去了,妈妈收回目光,此时等候着的所有亲戚都聚拢到急诊室门前的那张床边。那个躺卧着的没了气息的老人,是我的外婆。
外婆去世后一年,我生下了我的女儿。现在我也成了妈妈,而我妈妈晋升为外婆。
我妈妈退休之后,一度花了大量的精力在照顾外婆这件事上,外婆走后她一度无所适从。而当她听到我怀孕的消息后,脸上露出掩不住的喜色,她有了一个新目标,照顾那个尚未出生的小婴儿。于是我们继续生活着,在抚养小孩长大的琐碎日常中,很少会再想起外婆来。
我说过的,淡忘,早在外婆的死亡之前,已经开启了。
28
女儿四岁时,已经是个粉雕玉琢的可爱小人,而且很可能已经开始有记忆,因此我们决定带她进行一次长途的家庭旅行。
有一天我们赶早乘上了小火车,登上了瑞吉山。这是一座位于苏黎世和琉森之间的山峰,登高望去,能见到十分温柔的湖泊美景。小火车抵达山顶终点后,我们决定徒步进行后续的下山行程。我们下车后穿进山中的薄雾中,享受着清新沁凉的空气,慢慢地向下行进。偶尔会听见牛脖子上的铃发出清脆响声,需要向路边稍稍让一下。
下山的路并不算难走,但我仍然认为应当适当保护一下膝盖,我们间歇地会在长椅上坐一会儿。这个时候女儿有些坐不住了,她站起来宣布现在要跳一支舞。
“外婆在哪里啊?外婆?”女儿在召唤她的头号粉丝。
“外婆?”我也顺着她的话。
我妈妈应该是站到一边去给她的小姐妹发照片,此时我能从越来越重的白茫茫雾气中辨识到她的轮廓,卷曲头发,身形微胖。
我忽然有点恍惚。
“外婆?”我又叫了一声。
“哎,外婆来了!来看你表演啦。”我妈妈从雾里走出来了,脸上笑得看不出实际的表情。
“好了,我要表演了!”女儿审视着我们这些观众的准备程度。
我和我爸妈在长椅上排排坐,我识相地取出手机准备摄像。
山上到底是有点冷的,我打了个寒战,心想,便不由得往妈妈这里靠了一下。
在一片潮湿中,我们紧挨着,一起看完了这场稚嫩的舞蹈表演。
写作感想:
就像潜入水底。看见不一样的东西,体会不一样的呼吸方式。在最开始是完全的无措,但是慢慢把自己交给文字,享受水、习惯水,跟着珍妮的引导,慢慢地把自己意识中几乎被淡忘的那些小事梳理好、安放好。外婆离开已经多年,而只有在写完与她的故事,我才真正轻轻地放下了我们的关系。
编辑导师|珍妮
写作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注册针灸师
目前在西门菲沙大学学习小说和跨体裁(hybrid-form)创意写作。她喜欢在写作中让人物经历种种缘分巧合,发现内在的觉悟和成长。作品见于三明治,emerge25 等。
评语:
谢谢Pavo创作了这篇形式上有创意的非虚构。我很喜欢标题和小标题里体现出的丰富意象。精炼的分段让每一小节都像一小篇现代诗。
文章虽然没有强烈的故事弧线,但句子里优美承接的观点和修辞很柔软地推动了叙事的进程,这一点能够紧紧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关于外婆五感慢慢丧失的那部分很打动我。它不光写了对外婆的观察,更把视角提升,谈到人和外部世界的本质关系变化。
如何去爱,如何看待依恋,如何面对死亡?Pavo在这个故事里表达了很多跟这些问题的深入对话,相信它们会让很多读者产生共鸣。
10月「非虚构短故事」工作坊迎来全新改版,你可以自由选择心仪的导师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