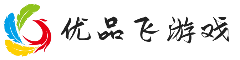大平台全新升级 大品正规官网 房卡 欢迎咨询 专注十年老店!!!
玩法详解:
2、打开添加微信客服【59722633】
注意事项:
邱士杰80后,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生
虽然电影并未结束在欢笑声中,我却是在从未停止的笑声中看完这部电影的。
宫崎骏的《起风了》(风立ちぬ)还没上映就已造成轰动。一方面,宫崎宣称这是他告别长篇动画的最后作品;另一方面,宫崎同一时间发表的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言论,也让这部电影和现实政治产生了联系。对于台湾人而言,大概只对第一个方面感兴趣吧。因此,不难想象,大概有很多观众,怀抱着如同观赏《龙猫》或者《天空之城》这样的心情来电影院。于是,当整部电影里虚构但诙谐的人物只剩下黑川(男主角堀越二郎的上司),所有希望看到笑点的观众便不断随着那唯一包含着笑点的人物而发笑(而且还有点强迫地要左右临众一起笑)。我实在不能掩饰我的不耐。
为了《起风了》,我两次走进电影院(看首场的时候,同行的观众其实都挺严肃,不愧是冲首场的影迷)。如果不是电影不好看,我想我也不会这么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了看部电影而两次走进电影院,很难想象我也这么做了。(我想起高中时代补习英文的时候,一个友校同学激动地跟我说:我看了《铁达尼号》五次!让我当场傻眼。)
《起风了》用画笔所描绘的日本,是新旧彼此交错的时代
片中的爱情桥段,特别是男女主角在火车站重逢的段落,总在脑海里萦绕不去。我大概是为了这个才看了第二次。想到动画也能表达出那种令人揪心的感觉,就觉得不可思议。可能这是因为我从未对宫崎骏抱持这样的期待吧。《起风了》虽然沿用了堀辰雄的小说名称,并声称描绘了堀越二郎的前半生。但更正确地说,是把堀辰雄笔下病恹恹的女主角拉出来,通过宫崎骏而与现实生活中的堀越二郎相遇。电影女主角坚强而自主,她抱病只身前往东京找寻堀越,并在病重之际决然地悄悄离开,只为了把最美的记忆留给他。这与原著小说的女主角性格不太一样。
如果真要说这部作品与其他宫崎电影的联系,性质最接近的大概就是公然表示宁可当猪也不当法西斯的《红猪》,以及隐藏了朝鲜战争与战后民主主义的《来自红花坂》。这是就作品本身镶嵌于历史脉络的深度来说的。相对于其他宫崎作品,《起风了》显得相当历史化。然而,我并不认为《起风了》因此显得直白。如果因为历史化而让观众少了诠释的空间,我想那是观众的问题,是观众为何失去了历史的问题。因为历史已经在你身上失去了,你才会觉得这样多的历史叙述是令人不耐烦的,甚至嫌弃其直白。
剧中,一位为了躲避纳粹而流亡到日本的德国人カストルプ(卡斯特鲁普)对男主角堀越二郎批判了希特勒,称希特勒们不过是一群流氓;カストルプ并批判了正在走向战争的日本,与中国战争,忘掉;建立满洲国,忘掉;退出国际联盟,忘掉;与世界为敌,忘掉。日本毁灭,德国毁灭。或者,当男主角从木盒中取出可以用来制作全金属飞机的杜拉铝,塞在盒内防震的报纸,大字写着上海事变(一二八淞沪战争)。这些历史情节乃至评价,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陌生了呢?或者,为何始终对于我们而言是陌生的呢?也许有些人认为这是宫崎骏的突兀之举,但或许,突兀的其实是我们所习惯的无历史。只需看看同样感到不快的那些日本右翼就知道了;狂言改宪并挑动战争的他们,正是失去了历史从而不再是历史主体的人。同理,我可以理解为何我第二次走进电影院时,同场的观众们如此欢乐,那正是因为已经有那样多的台湾人不知该如何面对《起风了》所要处理的历史议题。而欢笑声所体现的无措,就是从尾崎秀树到陈映真都批判的某种丧失症和白痴化。
震撼我的,不是一个有历史感的宫崎骏或者有历史叙述的电影,也不是这种历史感如何符合乃至满足于我的预想或期望。一切超乎我预期。我的共感,或许正源自于此。
超乎我所预期的感觉,是《起风了》所表达的近代的不超克(虽然很蠢,但姑且先用这个杜撰的说词吧)。众所皆知的自然是近代的超克,这是在太平洋战争展开的条件下,日本把欧美的近代视为超克对象而提出的一种思路。但《起风了》所想要说的,却是两战及其之间的日本,连起码的近代都追赶不上。从而,不是日本应该如何超克近代,而是如何首先实现近代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堀越们所开发的飞机用牛车拖拉到机场之类的现象如何克服而已。宫崎作为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肯定最起码的近代,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个侧面。就像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丸山真男(观察者网注: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被认为是日本战后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学者。1950起,经常演讲推动社会运动。1960年与岸信介内阁进行安保斗争后,受到批判,不再对现实问题发表看法。)所主张的那样。
自幼以来,堀越二郎不断在梦境中与意大利飞机设计大师カプローニ(卡普罗尼)对话。对话总是围绕着制造美丽的飞机而展开的
少年堀越:我的梦,我想这是我的梦。
カプローニ:这应该是我的梦,也是你的梦吗?你是说我们的梦连在一起了吗?这世界就是个梦。
青年堀越:我想建造漂亮的飞机。
カプローニ:真是一个美丽的梦。
西方的近代也是日本人的梦,但这样的梦是日本人能与西方人共享或相连的吗?至少,当カプローニ说这世界就是个梦的时候,否定了西方对于这个梦的垄断权,反正都只是个梦。虽然仍是从一个西方人的口中说出来,却是在另一个日本人的梦中。《起风了》所讨论的梦,也许就是近代吧,这个梦具有两义性。一方面,这个梦是在日本实现最起码的、至少以西洋为标准的梦;另一方面则是同时超越东洋与西洋。在东西洋同样陷入战火的时候,超越东西洋的梦的意义,便愈发突出。カプローニ说,飞机不是战争的工具飞机是美丽的梦想、当轰炸机太浪费了。堀越甚至提出认真但不得不让观众感到诙谐的想法:暖被炉(コタツ)能不能与飞机结合呢?
剧中一个重要的比喻是乌龟与阿喀琉斯的竞赛(观察者网注:阿喀琉斯[Achilles]是希腊神话中最善奔跑的英雄,哲学家芝诺设定他与乌龟赛跑,提出著名的芝诺难题)。西洋是远远走在之前的乌龟,但日本却是远远落后的阿喀琉斯。堀越的同僚认为日本只能当阿喀琉斯来奋力追赶(飞机制造水平),但堀越却说:小一点也没关系,难道没有成为乌龟的路吗?如果飞机(近代)不再是西洋所能垄断的,那么东洋究竟是要用乌龟的速度通向近代,还是用阿喀琉斯的步伐向近代跃进?堀越的回答似乎是宁可选择乌龟的近代。只是,战前的日本方方面面终究未能达到西洋近代,却把所有力气都放在提高武器与战争暴力的水平,意图以此力追西洋乃至意图超克西洋,最后只能成就一个二十世纪的畸形日本。
也许是因为在旅行期间认识了流亡在日本的反战者カストルプ,随后的剧情马上转入堀越无端遭到特高警察调查的状况。堀越生气地说:近代国家不允许这样的行为!他的两位上司却马上哈哈大笑:日本是近代国家吗?
《起风了》用画笔所描绘的日本,是新旧彼此交错的时代。高尚而美好的场景,都充满着西洋近代的风味,这也许是宫崎骏追求着起码的近代的证据之一。男女主角在火车上的首次相遇,在法文的对话中开始并结束,Le vent se l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虽然这是堀辰雄原著小说本来就有的,意为起风了,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此外,不断在剧中出现的女主角口头禅Nice catch,也让我这样一个外国人感到洋味十足。(我无法分辨这是否是当代日本人已然惯用的口头语。)只有在男女主角的结婚仪式以及夫妻生活的情节,或者童年时光,才能看到得到美好刻画的日本传统。
正因为是新旧交错的时代,因此也是不够近代的时代。日本军事工业的落后以及技术者亟欲赶超的心理,是《起风了》着重描写的情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试验机不断坠毁,马力不够的飞机引擎乱喷油,乃至飞机从日本的首艘航空母舰上落海。诸如此类。也许这部分的描述最让我感到陌生吧。因为这本是我在两弹一星工程之类的熟悉故事中,才能看到的叙述和情节。我却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当日本人拿着计算尺造飞机时,我们用算盘计算核武器的当量。当然,还是有所不同,日本的故事总是强调个别科学家或技术者的独特作用,但中国的叙述则着重于集体合作的力量以及日本无法想见的艰苦环境(狂风大漠之类的);日本的技术成果最终都直接服务于侵略战争,但两弹一星却是有剑而不用,当时的关键是在政治上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与核讹诈,阻止战争的发生。宫崎骏采用了我所难以想象的视角描绘了那个时代的日本,这种既陌生却又熟悉的感觉,正是我从中所获得的最大收获吧。
落后以及在有限条件下赶超落后的后果,就是以零战为代表的日本战斗机的出现。虽然是全金属战斗机,但因引擎马力有限,若要使火力强化能与速度及灵活度相配合,就必须尽力简省全机结构重量,特别是几乎取消了对飞行员的保护设施。根据堀越二郎战后的说法,军方认为长期来说还是必须强化对于飞行员的保护。但堀越也指出,战斗机的重点其实不是防弹,防弹是轰炸机之类的机种才需要重视的。易言之,飞行员的生命很容易成为消耗品,战争本身不得不表现出另一种劳力密集性。这是工业水平和资源条件追不上西方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于是,这也体现了战前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性:
据《日本资本主义分析》一书指出,日本资本主义的这种脆弱性决定着日本军队海陆装备的制约和它活动(战略、战术)的特殊制约。它表现在对飞机、坦克、装甲车、机关枪等向新式武器转型,同时对新式武器水平的对应制约,进而在战术上,由于军队机械化程度低,导致实行密集化作业和注重夜间操作。(田中正俊,《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73页)
剧中的堀越是矛盾的,他制造着他所期盼的美丽飞机,甚至是希望能够用来载客的飞机,但现实是,如果要制造理想中的飞机,当时只能是杀人飞机:杀人、被杀,以及自杀。宫崎骏为了表达这样的矛盾,并为了避免观众在故事的展开中走向他所不愿看到的误解,他很巧妙地让可能产生误解的剧情立即得到解消。比方,当飞机设计师们热情地讨论堀越所提出的新型战斗机方案时,堀越却吊诡地说:那些方案是不安装机关枪才能实现的。当剧情谈到日本轰炸机在战场上被击落,因此需要改良轰炸机的时候,画面上击落日本轰炸机的,竟然是涂上青天白日徽的中国战机(我没看错的话)。显然,这是中国战场,而日本飞机并不是无敌的。
据说宫崎骏是在确认堀越本人对于战争抱持相当的反省态度后,才决定制作《起风了》
关于零战的电影,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初期拍摄的《零战燃烧》。电影安排了堀越的角色,但剧中的堀越只是一个主任设计师,并没有太多的战争反省。而整部电影虽然叙述了零战从开发到战争结束的总过程,基本上仍然是一部歌颂侵略战争的电影。《起风了》并没有演到堀越设计零战,只演到堀越所开发的零战前身九试单座战斗机,而且基本上只演到开发成功(这与《零战燃烧》演到战争失败是恰好相反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歌颂成功的叙述,因为女主角菜穗子在同一时间离开了他。当菜穗子最终离开了他,始终戴着帽子的堀越也许帽子意味着某种理想也终于失去了帽子,失去了人生的追求。也就是说,恰恰是在这种形式上的成功深处,埋下了理想的实质崩坏。
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回来。这是堀越在电影的最后所说的一段话。失去了帽子的堀越与カプローニ站在最初相遇的梦中草原上看着远方飞来的零战,并看着他们一架架飞向天际间无数的机群之中那是《红猪》里曾经出现的阵亡机员所聚集的天河。
カプローニ:我们的理想王国。
カプローニ:因为毁灭了国家。
两人的梦终于连在一起,成为我们的理想王国。但此时,堀越却已觉得是地狱了。堀越二郎在战后撰写的《零战其诞生和辉煌的记录》(《零戦:その诞生と栄光の记録》,东京:光文社,1970)曾说,当他从报纸上知道许多拥有美好前途的年轻人,带着静静的微笑搭上他的飞机零战而去进行特攻之时,感到为什么日本要跳进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为何零战非得被这样使用,这事情始终萦绕在心。
平心而论,我不认为《零战其诞生和辉煌的记录》全书有百分之百的反省意识,只看静静的微笑这种违背常理人情的描述就知道了。该书其他部分甚至写到,他曾一边喝着味噌汤一边在报纸上看到他所设计的战机空袭中国首都南京并击落中国战机,于是不禁发出了HO!的声音。他在行文中所表现的激动情绪,对他而言我想并不是负面的吧。但对我们而言,只要联想到同年随后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融入那种看见自己的设计发挥威力的心情。究竟这种杀人武器何来荣光之有?
就此来说,宫崎骏不仅仅将女主角从堀辰雄的小说中拉出来并加以改造,就连男主角堀越本身,宫崎骏也做了相当的修正。虽然,据说宫崎骏在确认堀越本人对于战争抱持相当的反省态度后,才决定制作这部作品。然而问题的症结就像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争议那样,对于人数就是三十万的我们中国人民而言,固然没有屠杀论是不能接受的,但就连对抗没有屠杀论的二十万人论,我们也难以接受。对于曾经是受害国人民的我们来说,已经确定并内化的反省深度,形成难以动摇的情感记忆,就像田中正俊与古厩忠夫(观察者网注:分别是东京文献学派三、四代成员,反战史学家,研究中国史与中日关系。)提到中国老百姓往往愿意相信石达开当年没有死一样。情感记忆不可能没有值得深入反思的地方。但在加害国人民的反省本身达不到相同高度的条件下,往往难以要求受害国人民反思自己的情感记忆。这里存在着这样的两难。
也许现实生活中的堀越已经在自己份内尽力检讨了战争,或许也已达到二十万人论的水平,但相较于动画里面已然相对达到我想,首先应该只是相对达到三十万人论的宫崎版堀越,显然现实生活中的堀越还是反思不够,而宫崎的反思已然超越了他。虽然,作品的反省仍然仅停留在为什么只让日本自己的子弟上战场牺牲,而未能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掬一把起码的眼泪。这是我们作为受害国人民所绝对可以挑剔的。
为什么日本的国家会走上这样愚蠢的历程?也许愚蠢的不只有日本。但日本却特别为此虚掷了数百万宝贵的性命,以及国民经年累月的努力和积蓄。一句话,这是由于指导层的思虑和责任感不足,以及在政治上的贫困所致。恰恰是现在,我希望诚心英知的政治家出来吧。堀越二郎。
即便真实生活中的堀越仍有这样那样可以指摘的地方,以上这段饶富现实意义的话,还是足以作为本文结束前的注语。当然,与其期待政客,也许我们更应该寄希望于日本人民、寄望于中日两国人民的进步连带!
* 附记:电影里,在德国出现的逃跑者是我看了两次都不晓得前后脉络的安排。在此谨记。年底马上又要上映一部同样以零战为主题,却在歌颂战争的电影。届时再来比较吧。参考新闻:http://biz-journal.jp/2013/09/post_2979.html